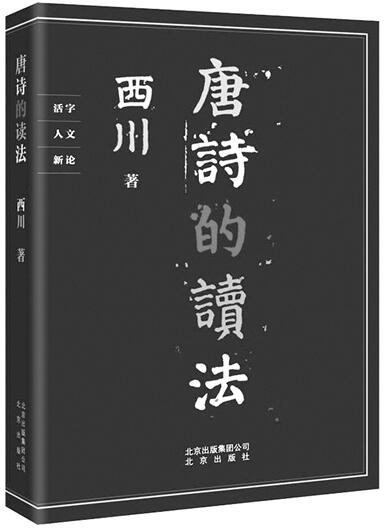
今年四月,西川的《唐诗的读法》一书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然而书中的主要内容则早已刊载在《十月》2016年第6期上,当时甫一刊出,就引起广泛关注。在《十月》刊出这篇长文后,曾有不少人认为西川提出了“唐诗的另一种读法”,但实际上,西川的读法,恰恰是古人最熟悉最常用的一种读法,正如这本书小引结尾所言:“《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有趣的是,《十月》的原文并没有这句话,西川之所以在书里补上这句,对此三致其意,兴许就是要提醒读者“知人论世”的重要性。而“唐诗的读法”这五个字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偏偏是唐诗?为什么不是宋诗或元明清诗?西川正是想带着读者回到唐朝读唐诗,回到唐朝的“当代性”。这个“当代性”既是唐人的当代性,也是今人的当代性,西川不仅要“进入前人的生死场”“努力把自己当作古人的同代人来读”,还要“再返回当下”,面对当下的问题,而所谓“当作古人的同代人”,正是《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
诚然,所谓的“回到唐朝”只能是对唐朝的想象,但当西川尝试将《全唐诗》甚至《全唐诗》以外的唐诗、类书、进士文化、安史之乱、道统论、牛李党争乃至诗人的交游逐一纳入他的观照中,将陈寅恪、傅璇琮、张国风、荣新江、李亮伟、贾丹丹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熔于一炉,兼收并蓄,尝试还原唐人所在的时空,这种想象不再纯然是空中楼阁,而这关键就在于“知人论世”。
正如西川所言,如今的人们“已经把唐诗封入了神龛”“供起来读”,或为写诗抒情,或为显摆修养,“通过背诵和使用古诗词”来获得一种“文化身份感”。联想到当今的“国学热”和“诗词热”,他这样的批评可谓相当尖锐。西川颇有微词地点出当代不少“诗作者和诗读者”的通病:“多愁善感、愁眉苦脸、自视高雅、自我作践、相信‘生活在远方’”。他指出,现代人往往“大规模缩小对唐人的阅读”,把唐诗局限在一些所谓的代表作中,意境唯美、风格典雅、语词浅显,甚至我们一相情愿地“扎进了进士情怀”,忽视了那些落第不得志甚至不曾留名后世的民间作者,忽视了张若虚仅存的两首诗水平之间明显而巨大的差异,忽视了那些顺口溜、打油诗性质的俚俗诗歌。但其实,如果只拿一部等同于儿童读物的《唐诗三百首》来读唐诗,只读那些“道德正确、用语平易且美好”的代表作,以“永恒的姿态”“提纯”式地阅读,无疑是以偏概全的,如入宝山而空手回。如果用西川的比方来说,“若以为熟读唐诗三百首就向唐朝看齐了,就相当于我们去曲阜旅游了一圈(还参加了当地的祭孔大典),就觉得自己接续上了儒家道统”。
这种以偏概全的提纯阅读当然并不只是今人所有的,陶渊明诗的艺术价值尚待宋代的诗人们读到《文选》之外的陶诗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估,明清的各派更是为了唐音宋调、宗唐宗宋的问题打了很久的口水仗,就连西川提到的李渔给出的女子学诗从晚唐开始的门径,多少也无视了杜牧作为军事家的一面,也未必会照顾到李商隐“韩愈体”的《韩碑》、学习杜甫的五言排律和高度复杂的其他诗作。我们固然可以说这个诗人、地域或时代的代表作如何如何,但往往这些“代表作”并不足以覆盖诗人、地域或时代的全部侧面。从这一点上来看,寒山、王梵志的存在,或许正是给浅阅读的读者的“一服清醒剂”。
只有当我们告别了浅阅读,视野从《唐诗三百首》扩大到《全唐诗》,甚至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器上那些失题佚名的唐诗,当我们注意到《文镜秘府论》里“随身卷子”之类的“技术性秘密”,当我们发现以诗赋谒公卿的重要性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写诗是唐朝文化人的生活方式”“是充足才情的表达,是发现、塑造甚至发明这个世界”,甚至这种生活方式渗透到民间,渗透到那些不见于《全唐诗》的唐诗的作者们——工匠或底层文人——那里,并且由科举考试和行卷制度得以推崇和普及,再加上帝王的表率作用、音乐与格律的发展、前代作品的影响,才塑造出这样一个诗歌的巅峰时代。诗对于古人,是他们生活的各个侧面的真实反映,既有隐逸的情调与豪迈的气概,也有文以载道的抱负与忧国忧民的情怀,绝不仅是单纯的附庸风雅,也不是浅尝辄止的文化味精。
在一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这样的观点势必会招来反对的声音。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及浅阅读只能让人理解唐诗“没有阴影的伟大”的问题,西川就解释称“阴影确定事物的真实”,并举出了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妃美术馆同时展出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和他为此做的大量草稿的例子,“只有知道古人写得不好的,才知道什么是好”。
不过,阅读量的由少到多,并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浅阅读的问题。在这样的当代语境下,非主流的唐诗和对典雅之作背后的创作秘密的揭示,自然最易受人关注,除书中所引的俚俗诗歌外,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出土的卜天寿的一首诗同样正中当代读者下怀: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这种浅白直露地抒发渴望放学、归心似箭的心情的打油诗,固然呈现出唐诗别样的风貌,但如果将这种阅读偏好推广到所有的唐诗,娱乐化、世俗化、浅显化,甚至抹杀了诗在古人观念中应有的严肃的那一面,那未免又入了另一种迷障。前些年中学语文课本上蒋兆和的杜甫像在网上一时大为流行,各种恶搞涂鸦传遍网络,时人戏称“杜甫很忙”,创作者对杜甫形象的改造与调笑,也反映出当代人已经不再能理解杜甫的诗风与儒家情怀了。就像西川所批评的:
“到了今天,人们在谈论杜甫这样的儒家诗人的时候开始强调其次要的一面,例如其率意、意趣,甚至顽皮,例如‘两个黄鹂鸣翠柳’‘黄四娘家花满蹊’‘桃花一簇开无主’等等。这样的诗句被娱乐化、生活化、去深度化的今人认为更能体现杜甫的本性,是杜甫更真实的一面——仿佛那个死里逃生又颠沛至死的杜甫反倒是刻意做出来的似的……”
如果说杜甫的创作在于安史之乱后主动抛弃了旧时代的审美趣味,破除原有的语言洁癖,不再仅仅流连于王维式的优美而绝对永恒的时空中,而是用诗歌直面生活,甚至介入生活,那么韩愈则在这场变乱的余绪中更笃于继承儒家的道统,攘斥佛老,尊崇师教,这种致力于处理当下问题的态度,可能也是他的诗奇崛拗硬、以文为诗、多用叙事的原因之一。西川就认为,韩愈对今人的特殊意义正是他独特的美学趣味。
这样的浅阅读,看似阅读视野拓宽了,观照到了杜甫、韩愈被选本遮蔽了的、鲜为人知的一面,但却“浅”在了理解深度上,其实是低估和矮化了这些大作家们原有的价值。这种读法当然渊源有自,明清人标举的“性灵”“神韵”,固然有补偏救弊之功,但当时之所以提出,是为了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相抗衡,是对《尚书》“诗言志”、《文赋》“诗缘情”与韩愈“文以明道”、周敦颐“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演变与对立的复现。
只是要我们在阅读唐诗乃至一切其他时空所孕育的文本时,都要去“知其人”“论其世”,要综合考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尽管过去近一个世纪中,新批评与结构主义在文学研究中大行其道,但回归文本并不意味着完全割弃作者与时代语境,尤其是产生于“知人论世”传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如果抛弃历史学、社会学和思想史的视角去看待它,把文学当成一种死的、与时代隔绝的永恒存在,那无疑是偏颇的。如果用西川在一次采访中的回答来说,那就是:
我不愿意让古典的东西蒙上尘土,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青铜器,都是绿色,那是铜锈,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青铜器在先秦、秦汉作为生活用具,一定是金灿灿的,我就在国外博物馆见过。
西川要做的,就是为唐诗“刮垢磨光”,驱散今人眼中蒙住唐诗的尘与雾,破除浅阅读带来的片面认识,让唐诗回到它的历史现场中放出应有的光来。
现在,西川的《唐诗的读法》这本书,恰恰就是要进一步补偏救弊,要恢复在现代主义和新批评到来前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解释学,思接千载,尚友古人,引领我们回到唐诗创作的现场,看他们的“当代生活、历史事件、时代风尚”,甚至看他们的“制度、古代思想、儒家道统”,不仅要“为唐诗祛魅”,更要充分地认识唐诗的伟大与厚重。只有告别了浅阅读,让诗歌介入此在的生活,文学与古人才不再只是“遗产”,不再只是“把玩一角风景、个人的小情小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川这本书吸收了不少学人的研究成果,将很多“远距离”的材料拉在一起思考,但我们也要意识到,这本书并不是唐诗研究的专论,甚至那些被媒体称为“新发现”的内容在学界眼里往往不过是常识,白居易的诗学观念到底是偏向闲适诗还是讽喻诗也有争议,背后的唐宋变革论、抒情传统等问题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而这本书本来也不是要单纯探讨唐诗的读法问题的。正像西川在书的开头所说的,“针对当代唐诗阅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给出看法,同时希望为新诗写作和阅读提供参考”,他永远是站在写作者的立场上思索唐诗的生成,这也是他与《六神磊磊读唐诗》等很重要的一点不同。
西川不想抛开历史语境去回应当代人对新诗的质疑,也无意回答唐诗成为巅峰的原因,而是去反思唐人在他们的“当代”中如何写作,从而让唐诗放射出它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原有的光辉,再照进我们当下的写作。西川强调的“在场感”,强调的杜甫、韩愈、李商隐针对“当下”的战乱、纷繁的思潮乃至个人的仕途处境所采取的直面态度和处理手段,从唐人的写作现场回望我们自己的写作现场,目的仍是指导当下的诗歌写作,而这或许就是《唐诗的写法》最大的意义。(繁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