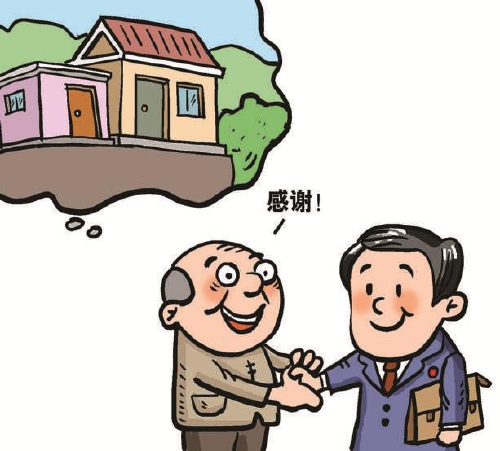
姚雯/漫画
前不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检察院收到了一起强拆案件的监督申请人老潘提交的撤回监督申请书。老潘在申请书里写道:“今年的洪水太大了,想着都后怕,要不是你们帮我协调异地搬迁,我们一家人可能都被冲走了。我不告了,我要好好过日子……”
今年6月,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洪水肆虐,很多村庄和道路被淹。当洪水漫过老潘家的老屋地基时,一家五口人已住进了安全的新居。一场持续3年的行政争议,也随着老潘一家居有所安、心有所归而得以实质性化解。
未批先建
新房遭强拆
“房子拆了,一家五口住哪里?我当初申请了,是政府没批下来啊。”老潘站在被夷为平地的新房前,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建房申请书》,声音里满是委屈。
2021年,老潘位于黔东南州凯里市某村的老屋遇地质灾害导致地基塌陷,屋体倾斜严重,墙面多处开裂。镇政府与相关部门到现场查看后,都认可老潘家的房屋存在安全隐患,不适宜继续居住,遂向老潘口头承诺会在政策范围内特事特办,允许其另建住房。以为吃了“定心丸”的老潘赶紧向村小组、村委会申请建房。大家考虑到他们一家的实际情况,一致同意他们新建房屋。得到村里的认可后,老潘立即向镇政府提交了新建房屋的申请。
想着已经提交了申请,批复是早晚的事,为了尽快让一家人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家,未拿到建房批复的老潘向亲朋好友借了钱,就近在自家老屋旁的耕地上修建了新房。
2022年11月,镇政府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老潘占用耕地修房,以“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为由,认定该房屋为违法建筑,并依法实施了强制拆除。
“我们开过村民小组会,村里都同意,镇里也来人量过地基,以为没问题才盖的。”在老潘看来,“村组点头”“政府丈量”便是建房的“通行证”,却不知自己的行为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新房被强制拆除后,老潘一家只能搬回岌岌可危的老屋居住。
不服判决
申请检察监督
2023年2月,老潘因对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恢复房屋原状并赔偿损失。“建房明明花了40多万元,为什么判决赔偿的损失只有1万元?我不服!”一审判决让老潘愤愤不平。
原来,一审法院查明,案涉房屋占用的耕地属于农用地,该房屋是在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违反土地管理法强制性规定情况下建成的,属于违法建筑,镇政府的强拆行为所侵害的权益不属于“合法权益”。尽管该行为因“超越职权”应当确认违法,但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合法权益受损时才能获得赔偿。因此,一审法院仅判决镇政府对强拆过程中被填埋的门窗内框、废旧钢材等合法财物赔偿1万元,驳回老潘的其他诉讼请求。
老潘不服一审判决,向黔东南州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同样认为,老潘在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行政许可手续的前提下占用耕地修建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不属于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赔偿范围,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后,老潘向贵州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再审认定“农户建房需遵循‘先审批后建设’的法定程序,即便政府在审批中存在瑕疵,也不能改变房屋‘违法’的性质”,于是驳回了老潘的再审申请。
老房岌岌可危,新房被夷为平地,看着居无定所的一家老小,老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于2024年9月向黔东南州检察院申请监督。
深入调查
厘清争议焦点
“法律不保护违法建筑,但要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受理案件后,为进一步厘清案件的争议焦点,承办检察官多次深入老潘所在的村寨走访调查。
“他家那个房子真的没法住,要不然谁愿意借那么多钱修房子”“当时村里开过会的,我们都同意他修房子”“一家老小现在都住在那个破房子里,确实可怜”……在走访过程中,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着老潘一家的处境。
经调查核实,检察官认为,老潘家确系“一户一宅”,且经过专业机构评估,该宅基地原址存在严重的地质灾害隐患,难以通过灌注水泥等加固方式恢复承载力,不宜在原址翻建房屋,除了属于基本农田的案涉耕地以外,老潘无其他林地或土地可申请转为宅基地,村里也无宅基地可供其申请使用,其建房确实出于基本生活需求。
而镇政府在收到老潘一家的建房申请后,未及时审批,亦未及时告知不能及时审批的原因,导致老潘陷入了认识误区。而且,在强拆过程中,镇政府工作人员未妥善处理建筑残值及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就直接进行了填埋,存在履职瑕疵。
“现在钱没了,房也没了,我哪里都不去,就要一个说法,这房子要是塌了,就住镇政府去!”老潘对上门了解情况的检察官说。
宅基地与耕地的界限不仅是土地权属的分割线,更连着农户安身立命的根本。虽然案涉房屋是未批先建,属于违法建筑,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不属于应当赔偿的范围,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但老潘修房确实是为了满足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且镇政府在履职中也存在瑕疵。在原址无法重建,新房又被拆除的情况下,一家人的居住权如何保障?这不仅是老潘的心结,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
承办检察官向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调阅了村规划、安置房布局等材料,并先后3次组织镇政府、村“两委”、老潘及其代理律师进行座谈,了解到老潘因建房已负债30余万元,无能力再向他人购买可以转为宅基地的土地,而其所在村寨属于城乡规划范围内,目前也无宅基地可供申请。老潘一家现在住的老房已经属于危房,每逢雨季,都有发生自然灾害的风险,镇政府虽然多次劝说老潘一家异地搬迁,但是老潘既不信任也不配合,导致争议化解陷入僵局。
化解矛盾
实现居有所安
“雨季即将来临,如果不及时解决老潘一家的居住问题,一旦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后果不堪设想。”老潘一家的居住安全问题,让承办检察官金亦贱忧心不已。
虽然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并无不当,但是无法接受赔偿数额的老潘还一直和家人居住在地基塌陷的老房中。为赶在雨季来临前化解该起争议,金亦贱同时对老潘进行释法说理,告知其案涉耕地属于基本农田,无法通过补办审批手续予以完善,案涉房屋必须强制拆除,并对判决确定的赔偿金额的合法正当性进行了说明,同时,积极协调镇政府主动向上级政府汇报,通过申请国有房源异地安置的方式解决老潘一家的居住难题。
化解方案有了,但是房源申请和审批却需要一定时间。今年6月,看着气象部门不断提示的暴雨预警,为确保安全,检察官再次冒雨登门,耐心说服老潘,帮助其一家五口紧急搬至村委会暂住,并联合镇政府立即启动应急救助,加快落实老潘一家异地安置事宜。
在洪涝灾害的影响下,老潘所在的村子没能幸免,洪水漫过村庄,老潘家那座老房被洪水冲毁。好在洪水来临前,经过检察机关的持续跟进和协调,老潘一家及时搬进了安置小区的新房。新房宽敞明亮,水电设施齐全,小区环境优美,老潘的两个孙子也就近入读了安置小区附近的小学。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家人的居住问题解决了,居住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老潘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他主动向检察机关撤回监督申请,案涉行政争议得以实质性化解。
“农村土地是个宝,乱搭违建不能搞,按章建房日子好。”这句顺口溜成了老潘平日里常挂在嘴边的话。如今的老潘,不仅和妻子在县城有了新房,还申请成为村子里的志愿调解员。他说,想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村里人,任何时候都要按规矩办事,出了问题也要相信法律,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才是硬道理。
这场纠纷的化解,既坚守了“违法建筑不受保护”的法律底线,维护了土地管理秩序,又彰显了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民生的司法温度,成为流传当地的一段佳话。
■检察官说法
不止于“结案了事”,要实现“案结事了”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往往历经行政决定、行政复议、行政审判等多个阶段,环节多、周期长,矛盾尖锐,甚至存在严重的社会戾气和安全隐患。进入检察监督环节后,申请人往往把检察机关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而通过做实高质效办案,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正是检察机关的价值追求和职责所在。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禁止擅自在耕地上建房”;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等规定,老潘擅自在自家耕地上建房,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是违法建筑应当依法拆除不等同于老潘的合法权益不受保护,因此,法院依法判赔1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在法院判决并无不当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通过积极开展释法说理,消除申请人的认识误区,坚守法治底线,维护审判公正和权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案涉违法建筑虽然应当依法拆除,但老潘一家住有所居、居有所安的基本生活需求应当予以解决。检察机关通过与行政机关形成工作合力,促成案涉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体现了检察办案不能止于“结案了事”,更要做好“后半篇文章”,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